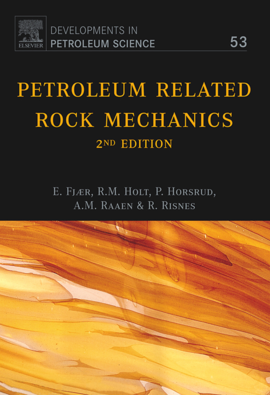大四课堂留下的都是什么人?怎么读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
二战前,美国的理科教育普遍不如欧洲。
现在,欧洲不如美国。
北京大学今天的生命科学本科课程优于剑桥、牛津的本科课程,远优于哥本哈根等一般欧洲大学。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水平,基本可以说,总体是空前提高。
但是必须清醒:除了与国外先进水平还有差别之外,现在也非一切比以前好。例如,几乎全部生命科学的研究生受教育的水准没有达到杨振宁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物理学研究生教育水平。
作为曾经多年为研究生教育提高质量做出过努力的人,不得不说:我国的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迄今水平还不够高,但是现在在很多单位已经有充分条件可以做好。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可能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得的硕士生教育优于今天大多数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的博士生教育,特别在课程的深度上。
杨先生的老师,是一批在国外顶尖学校回国的优秀青年教师。他们在中国缺乏研究条件,有时间对学生的教育非常上心。
中国早期回国的生命科学学者,除了少数学了现代科学,有些学了后来没有发展的方向,有些本来就比较粗浅。1976年后新出现的研究生导师大多数是没有经过研究生教育,不仅没有经过国外的研究生教育,也没有经过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当然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历史缘故)。
1980年至2000年的(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育体系,是低标准的。
2000年后,虽然有些学校有一些经过较好研究生教育背景的人成为老师,但人数太少,各种工作繁多,能够投入研究生教育的人力缺乏。
有鉴于此,我和吴家睿在2000年发起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课程(初期称为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各一个学期,后称为BIO2000,一个学年),请国外一些教授回国系统讲课。我主持最初三年,之后交给其他老师。2003年开始也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一共十几年。
这一课程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唯一的特等奖课程。
它在一段时间确实很好。但后来有一位主持的北大老师不负责任,也有其他课程质量提高的原因,这门课程不再特别。
我和一公都在两校建立研究生体系,也鼓励建设研究生课程。
回顾起来,我们很多改革非常成功,但研究生课程可能是做的最差的部分。究其原因,首先是改革的事情繁多,孰先孰后(我们显然重点以教授体系的建设为最优先)。其次是课程建设实际需要老师的相当投入。第三是当时深刻认识研究生教学的老师还是不够多。
今天,很多学校都拥有足够的老师,能够担负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只缺老师的愿意投入和学校的督促。
今年秋天,我被7个不同的老师,邀请参加他们负责的课程讲一次(有一小时的、有三小时的),我发现基本都在同一个层次,要么是“导论”课程,要么是“进展”课程。
这两种课程,对于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是远远不够,而且是非常偷懒的课程。
研究生的导论课程实际很像本科生的课程,而进展课程一般都成为老师讲自己实验室的研究,用于招募学生。
这是不够的。
我们中国的研究生,需要培养一批有高度和深度的科学家,其起步课程亟需改造。
1985年至1991年,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读研究生,课程是这样安排的:
作为神经生物学的研究生,我必修:一个学期的神经生物学原理,一个学期的分子神经生物学,一个学期的细胞神经生物学,一个学期的发育神经生物学,一个学期的系统神经生物学(分别有一位老师主持,几位老师讲课,主持分别为:Zach Hall,Roger Nicoll/Jim Hudspeth,Louis Reichardt/Yuh-Nung Jan/Jenny and Matt LeVail,Mike Stryker)。还听过感觉神经生物学(Mike Merzenich)。
神经生物学规定学生必须全校的“细胞生物学”。全世界通用的《分子细胞生物学》教科书是我们学校生物化学系主任为首主编、1983年第一版,现在风靡全球。近四十年来,全世界最重要的生物学教科书就是Bruce Alberts的《分子细胞生物学》。他后来曾任美国科学院院长、《科学》杂志主编。除了DNA复制研究出色、发明亲和色谱方法外,教育是他推重的。
我们的“细胞生物学”课程1985年主讲是Peter Walter、Marc Kirschner、Mike Bishop、Henry Bourne、Judy White等。分别是:早期signal peptide过膜实验而推动其自己导师获1999年诺奖而以后自己实验室工作导致现在因为非折叠蛋白质反应而候选诺奖、微管蛋白和细胞周期重要发现科学家后创哈佛系统生物学系、1989年诺奖得主、G蛋白偶联受体权威、融合肽新星。
我自己还多修了生物化学系的两门课程: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遗传学的老师是Ira Herkowitz,在细菌和酵母遗传学都有重要贡献,当时任美国遗传学会理事长。讲课特别循循善诱,引人入胜,是我一生遇到的最会讲课的老师。果蝇遗传学的老师是Tom Kornberg,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诺奖得主,他先读Julliard音乐学院、后获剑桥生物博士。1980年代,他与Pat O'Farrell实验室首先证明homoedomain结合DNA、调控基因转录。
我修了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分子生物学课程,UCSF称为Biol Reg (Biological Regulatory Mechanisms)。发起的是Keith Yamamoto,和Christine Guthrie。我学的时候他们和 Nancy Craig 、 Sandy Johnson是讲课老师,讨论课辅导老师是Rick Myers。因为留学有很大担心的第一年都是A,研二有些掉以轻心、留美第三学期有些贪多,修了两门神经生物学系非必需、而生化系著名的难课,而身体遭遇甲状腺疾病,后决定集中精力把“遗传学”开完,而中途退出Biol Reg,到第三年再重修,以便达到效果。研二得过一辈子唯一的“I”(incomplete)。其内容丰富和深刻,等到不生病的时候重修完全值得。Yamamato是基因调控的专家(特别是糖皮质激素基因调控)、Guthrie是酵母RNA剪接专家、Craig是DNA重组专家。这门课我私下最高兴的是在听课时,老师没有讲,我意识到染色体末端的复制是教材还不能解释的,在课堂上提问才知道是已经有人在专门研究的。研究的科学家当时还在UC Berkeley,后来搬到UCSF生化系(2009年获诺奖)。
在遗传学之外,我修或旁听了一个学期的“人类遗传学”。老师是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理事长Charles Epstein和David Cox。
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结构生物学,老师是Bob Stroud和Bob Fletterick。
旁听了一个学期的发育生物学,主讲是Patrick O'Farrell。
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病毒学, 老师是Harold Vamus、Mike Bishop和另外一位。
UCSF的研究生一般是前两年有必修课。我在第三年还修过,另外旁听一些。完全没有课的学期,旁听一门课是非常简单而且很有效。
我做老师之后也想过每学期旁听一门,但完全没有做到。非常可惜。
学生时代学过的,一般比较投入,而以后追踪同学科的研究就比较容易,非常有助于积累。
在修过课的基础上,加上学术报告,系统读专题文献和浏览一定范围的文献,对建立学术文化至关重要。
以前中国很多研究生导师没有这样的经历,而今天很多研究生导师有类似以上的经历,所以就应该给学生提供很好的研究生课程和研究生教育。
以上举例希望说明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生课程,必须深于本科生课程,必须告别“Introduction”和“Progress”两门,而给研究生提供本专业多门课程,同时几门其他专业的课程供选修。
如果学校和老师不提供这样的条件,我们每一个有自我激励的研究生,应该自己想办法,包括大量阅读文献,积极听学术报告,特别是好的学术报告。
本文之所以不提科学研究,是因为老师一般都有动力做好研究,不需要文章来鞭策。
附录
最近,PNAS刊登悼念Christine Guthrie的文章:她母亲是作家,单亲家庭,母亲把她写到小说里面,美国电视剧连续播放。
她短暂结婚获得的Guthrie姓,一直用是因为她第一篇论文用了,后来就没有改。
她过了一些年与加州理工学院的John Abel结婚。
她在研究阶段(包括在德国做博士后)感受到性别歧视。
她于1973年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系任教,此后13年,为该系唯一女教授。(这个说法意思是生理学系教授兼 职生物化学的没有计,因为叶公杼夫妇是1979年到UCSF任教,主聘生理系,后兼任生化系)。
招聘她的系主任去世后,她曾经抑郁症。
她早期研究tRNA,1979年之后改研究RNA剪接,用酵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