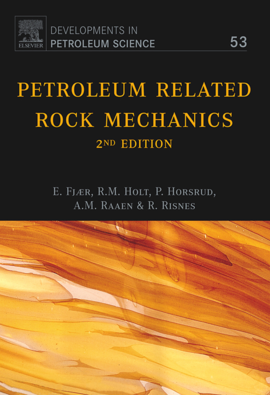荐读|陈平原:不注明出处就算抄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时候,我们写文章,必须不断地给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认同的东西,加一个注?那是晚清才开始的。”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本文摘要:(由ai生成)
陈平原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中讨论了学术写作中引文的重要性。他指出,晚清以来,学术写作需注明出处,与古代做法不同。20世纪前后,引文处理成为学术关键。引文有多种形式,各有用途。传统文人喜用典故而不标出处,但清末开始强调注明。陈平原认为,在尊重前人基础上构建学术并维护文章完整性是重要议题。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李浴洋博士曾在文章中称,《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书末两篇附录——《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如何‘述学’,什么‘文体’》,与精心撰写的《前言》一道,道出了陈平原从事此项研究时‘压在纸背的心情’。”
本文即摘自该书的“附录一”《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谈“引文”部分。
登录后免费查看全文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欢迎分享,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首次发布时间:2024-05-05
最近编辑:6月前
作者推荐
还没有评论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